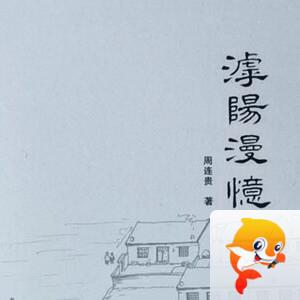38长篇回忆录《滹阳漫憶》第十章生命承受之重(1)一部农民写的书
38长篇回忆录《滹阳漫憶》第十章生命承受之重(1)一部农民写的书
2023-06-13
阅读 4895
和兑✨云
播讲: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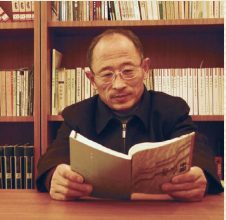
本书作者周连贵老先生,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,1944年出生于河北省沧县马连坦村,读过小学、初中,高一时,因生活贫困无奈辍学,从此便拿起了锄头,成了名符其实的农民,在半个多世纪的农村生活中,老人经历了初级社、高级社、人民公社、土地承包责任制、改革开放、现代化以及小康社会诸多历史阶段,老来生活安逸,闲暇时老先生拿起了笔,给我们呈现了这部近二十万字的长篇回忆录《滹阳漫憶》,让我们一起跟随着老先生平实朴素的话语去听一听他的故事,去看一看上世纪华北平原乡村数十年的变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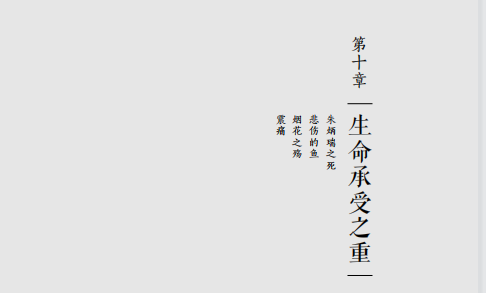
第十章 生命承受之重
朱炳瑞之死
悲伤的鱼
烟花之殇
震痛
朱炳瑞之死
提起朱炳瑞,二十刚出头,小伙子长得精神帅气,给他的一个寡妇婶母过继。刚结婚一年多,小两口十分恩爱,并百姓是他的一贯手段,因此平民百姓都惧怕他三分。村里每有集体出工,带队的人非他莫属。
一九五八年成立了人民公社,全国掀起了大跃进运动,就在这一年的秋冬之际,对村南边的滹沱河进行了开挖治理,村子里的带工人就是他。由于处于大跃进的年代,挖河工地也是热火朝天,各种纸质的彩旗插遍工地,上面写着顺应时代的口号。小学生也排着队伍敲锣打鼓前来助威,各村的带工人组成评比团。当时制作了一面流动红旗和一面黑旗,最先进的便把流动红旗插到他们的工地上,开大会进行表扬,最落后的当然只有黑旗伺候着,并挨批挨训,使带工人颜面扫地。
为了争夺这一面红旗,各村的带工人都使出了看家的本领, 监督民工拼命干。李某在全村民工大会上郑重其事地宣布 :“你们要是让我扛回黑旗来,你们都要拿命来见我。”可见那一面流动红旗对当官的来说有多大的诱惑力。
李某每天都躲在暗处观察着民工的一举一动,发现有问题,他便当场施威,或到大会上批斗。有一次,民工李煦化去出恭,李某远远地盯着他。过了好长时间,李煦化回来了,他便走到李煦化蹲下去的地方检查,结果发现李煦化排出的粪便一点点。到了晚上便召开了批斗会,会上让李煦化脱光上衣,在寒冷的夜晚迎风站立。李某开始讲话了,他说:“李煦化这个黑小子纯粹干活儿磨洋工,拉屎蹲了一个来钟头,只拉了像根江米条那么一点点。”说这话时还用手指比划着。他说:“你们别看我眼睛小,就是管事,哪一个偷懒耍滑头,也逃不出我的眼睛去。”就这样把李煦化批评到大半夜。还有一次,民工李名服因当场顶撞了他几句,李某让李名服坐着“飞机”沿着河堤游行示众。那个时候坐“飞机”是整治人的土办法,就是让李名服猫腰,低头九十度双臂向后翘起来,稍有松懈,后面就用脚去踢,这一次把李名服折腾得苦不堪言。还有一次,李煦化正举着洋镐在开冻,他每次都是高高地举起轻轻地落下,这一举动又被李某发现了,他便走过来对李煦化说:“你再把刚才开冻的那两下拿出来我看看。”李煦化是吃过他苦头的,在他的威逼下不得不照老样子演习一下,把洋镐高高举起又慢慢落下。这一举动一下子激怒了李某,他说了一声“我打死你”,顺手从民工肩上夺过了一条抬筐的扁担,双手抡起来就向李煦化打去。李煦化眼看大祸来临,便双腿一弯给李某跪下了。这一跪,李煦化免除了一顿皮肉之苦。这样的酷吏老百姓怎能不怕?按理说,李煦化、李某都是李姓一家人,李煦化还长李某一个辈分,李某给李煦化下跪才是正理,现在反过来,当叔的却给侄子下了跪,这天理人伦安在?
话说朱炳瑞来到治河工地,每天打打闹闹地活跃在工地上。有一天,他突然感到肚子疼,于是就回到驻地休息,李某知道后便说他是在装蒜,非得逼他去上工。此时的朱炳瑞真情实病,说什么也去不了。到了下午,李某又施展了淫威,他说:“你们给我找个锭杆子来,我专门会治肚子疼,用锭杆子一扎就好。”要知道这锭杆子是农村妇女用手摇纺车纺线用来穿线用的,两头是尖,有一尺来长。李某却要拿它来治病,真是惨无人道至极。
到了晚饭时,朱炳瑞已疼得实在支持不住了,满地乱滚,大呼小叫,豆大的汗珠直往外冒。李某一看是真的得了病,且病情很严重,这才组织人绑好了担架,抬着朱炳瑞向沧州医院奔去。由于延误了一天的时间,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机会,走到半路朱炳瑞便一命呜呼了。
这时李某才真慌了神,派人连夜赶回家中,向村干部报告了噩耗,并隐瞒了当时的实情,朱炳瑞的尸体被抬回家中后便草草掩埋了。失去丈夫的媳妇后来带着幼小的女儿改嫁了,孤寡的婶母在痛失嗣子后也远走他乡,就这样好端端的一个家庭被弄得家破人亡。
朱炳瑞的老父亲是富农份子,在那个年代,地富反坏右被打成黑五类,是阶级敌人。每逢有运动来临,这些地富分子是首先挨批斗的对象,躲避唯恐来不及,哪里还敢去伸张正义,有冤只有埋在心底,默默承受着。就这样,一个草菅人命的酷吏竟然逍遥法外,真是天理难容。这位称霸一时的凶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受到了应有的审判,被逼得跳过井自杀,没过几年,被癌症夺去了生命,年仅四十多岁。他死在了大年三十晚上,村里没有一个人去吊唁,显得异常冷清凄惨,这也许就是上天对他的惩罚吧。
悲伤的鱼
在中国农村流传了几千年的封建思想,至今仍然存在。比方说多子多福,多子多寿,每个家庭至少也要有一个男孩儿传宗接代,延续香火。
一家人不管有多少女孩儿,只要没有男孩儿,总不肯善罢甘休。这里面还有一个伦理观念在作怪,古人云,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,认为没有儿子也是对长辈的大不敬,农村还有一种说法,就是没有儿子是上辈子没有做好事,这辈子让他断子绝孙,所以在农村,一家有四五个以至七八个女孩儿的屡见不鲜。
我们村的朱炳昌,人到中年,已是四个女儿的父亲了,只因为没有儿子,总觉得不甘心,终于在一九六六年的春天,得了个宝贝儿子。儿子的到来,给全家人带来了欢乐,也给邻里乡亲带来了喜悦。在生产队集体劳动时,总是一群一伙的,有一次下地干活儿,走在半路上,闲谈涉及了他的儿子,有人说:“你这也算老来得子,应当给儿子做百岁庆贺一番。”朱炳昌说:“还做什么百岁,都过了一百天了。”社员李明良打趣说:“既然过了一百天,那就做二百岁吧。”朱炳昌说:“哪有做二百岁的?”李明良接着说:“过去那皇上一千岁一万岁,都跟闹着玩儿似的,怎么做个二百岁你就嫌多啦?”一句话逗得大伙儿哈哈笑。
朱炳昌的儿子虽然是根独苗,但却起了个乳名叫成帮,那是预祝后代子孙兴旺发达、成群成帮的意思。小成帮在父母和姐姐们的呵护照料下茁壮成长,到了八九岁长得很结实,已经能为大人做一些简单轻松的活儿了。
朱炳昌爱撒鱼,每天生产队放工后,他总是背上渔网到河里撒一阵子,不管网的鱼多少,这成了一种嗜好,一种乐趣。每次撒鱼,总有一个女孩儿提着小桶跟在后面拾鱼。随着小成帮的长大,这拾鱼的差事便由他代替了姐姐们。朱炳昌也乐意把这个长大的儿子带在身边,因此人们经常看到这一对打鱼的父子出现在河边上。一九七七年秋天的一个下午,放工后,12 岁的小成帮又提了个小鱼桶随着父亲去撒鱼。爷俩儿顺着河的南岸一直向东,一网一网撒出了村子。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,也许是朱炳昌的兴致大发,也许是鱼太多吸引住了他,以致出了村子很远仍不肯往回返。天越来越黑,余兴未尽的朱炳昌忽然发现后边的儿子趴在高压线上,他赶紧跑过去,儿子被电线紧紧粘住了。他知道用手去拉不行,于是他就抡起渔网向高压线打去。线是被打开了,朱炳昌也被弹出去老远,再看孩子已经没气了,折腾了半天也没缓过来,只好抱着死去的儿子哭着回家了。这一下给全家人带来了沉痛的打击,人死不能复生,只能面对现实,强忍悲痛,掩埋了儿子。这时朱炳昌才发现自己的脚也被严重烧伤,儿子入土,他也住进了医院。
在医院里住了两个多月,由于伤势过重,不得不截去了两根脚趾头,最后也落下残疾。我们村是在一九七二年才办起了电网,人们对电的危害还没有足够的认识。为了利用河水进行灌溉,在村东边架设一趟过河的动力线,其中有一根从线杆上脱落下来,离地面最低处也就一尺多高。电工周连新曾多次提出把线架设好,可大队上的一位干部却说甭管它,没事的。就这样这根电线在那里不知摆放了多长时间,直到朱氏父子酿出惨剧,造成一死一伤的结局,这才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沉思。
本期制作:云
期待下集更精彩
特别声明: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,VV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。
作品已不存在或设为私密
点赞
点个赞抢个沙发吧~~
更多>
点赞用户
加载中...
1429
0
文章评论未开启!
0
167
分享
扫码下载VV参与互动
复制链接成功!


和兑✨云
喜欢文学和朗读,喜欢徜徉在声音的海洋里,用声音来演绎人生百态
关注
TA的作品
热门文章